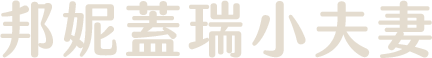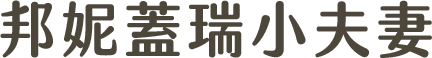最近有一個病房,走過時總會充滿小孩的笑聲。
兩個小朋友,一位3歲,另一個不到1歲,兩個人由爺爺奶奶帶來探望爸爸。不知道是不是總在爸爸的病床旁看到許多親戚們,看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笑嘻嘻的。
爸爸36歲,月初覺得肚子疼痛,先是在台東當地醫院檢查過後,在大腸看到疑似惡性腫瘤的病灶,腹腔看到許多腫瘤以及惡化快速的腎水腫。在醫師的建議下,他來到台大醫院就診。
稍微有醫學背景的人,看到這樣的病史多半心知肚明。
手術馬上被執行,在術中取出的部分腫瘤組織送病理化驗,而診斷也被大大的寫上:大腸癌併多重腹腔轉移。儘管正式報告要等待病理結果出來,但癌症末期幾乎是可以確定的。
第一次接觸到這位爸爸是在他大腸癌切除手術後。手術前,他承受巨大的疼痛;手術後疼痛依舊,現階段的手術也只能將最明顯的大腸癌病灶切除,腹腔的腫瘤轉移壓迫仍讓他痛得不能自己,所有能給予的止痛藥都無法緩解這樣的疼痛。
記得在值班的夜晚,默默站在他床頭看著他因痛楚而痙攣的臉,一旁多天沒睡的太太眼眶浮腫。
我永遠記得那充滿沮喪的一夜。學了多年的醫學,看著外科老師們多次的拯救病人。但這一次,醫學在死神面前只顯得渺小而卑微。
隔天早上,在例行性的訪視病患中,他主動叫住了我。
「醫師,我的健保卡給你們看,在台東時我們有簽過DNR,上面不知道有沒有註記不要急救。」他指著櫃子上的健保卡。
DNR,代表著放棄維生急救治療。當病程只會不可逆的邁向死亡時,病患與家屬有權選擇不接受醫學的維生,在安詳中離去。
「朋友,我一開始不是就跟你們講,可以老實跟我講我的病情嗎? 我OK的。」
在他轉到病房的一開始,我們就知道他有兩個年幼的小孩,也因此,他這樣不樂觀的病情,沒有人敢貿然告訴他。
而是在他多次治療後昏睡時,委婉的告訴他太太與爸媽一切。
然而不知何時,這位爸爸輾轉感受到他病情的嚴重。
「我OK的,來吧! 可以告訴我!」
他那不合時宜而豁達的笑的背後,必定是無數的淚水與無奈。
他這階段的大腸癌5年存活率統計上只有11%,而他的情況只會更差。除了大腸癌多重轉移外,大量腹水、急性腎病與肺栓塞也在一個月內前後來報到。
「我們是台東卑南族的喔! 跟歌手阿妹一樣,都來到這邊了,一定要加油!」在知道病情後,他握了握拳頭。
即便這樣說,但那清楚的DNR聲明,他太太滿臉的淚水,總讓他的打氣顯得無力。
在我們訪視完後,兩個小孩又被爺爺帶回病床,滿心期待的找最近一直在打瞌睡的爸爸。
每次經過他的病床,我總會駐足,默默的看著他一家人,看著他和太太對著小孩的童言童語報予淡淡的微笑。
兩個小孩的天真懵懂難掩癌末的離愁,死神的呢喃讓病房總充滿嘆息與婆娑的淚眼。
病患的病床有著面向東方的窗戶,他每天都會看著黎明升起。
「我家住在東部,不過現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了。」他總苦笑道。
或許是他的身體告訴他,在DNR簽署並且拒絕所有維生醫療後,他很可能一步也踏不出台大醫院。
昨夜小樓起東風。人生何許,多次醫療處置換來一場空,生離死別仍然近在咫尺。
每一個天明,兩個小孩總早早被帶來醫院。
在值班後的日出,我站在病房外,看著他們一家人背著暖紅日光的剪影。
他摟著女兒與兒子輕聲細語的交談,兩個小孩則開心的笑著。
昨夜小樓泣東風,低聲望著日空,我多麼希望他們能一起再回到台東。
他遠遠的看到我,給我一個微笑,舉起左拳握了握。
「加油!」我看到他的嘴型,與微笑背後的堅定,一個我無法想像與做到的堅定與樂觀。
慚愧的是我只能擠出一個笑,連加油也不知為何說不出口。
唉,昨夜小樓又東風,可惜東風又作無情計。